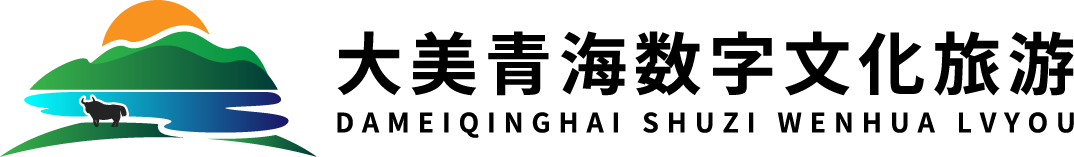五十年代,尕布龙同志在河南县与牧民子女在一起。 (资料图片)
一个牧人一样的公仆,一个公仆一样的牧人。
——摘自本文以作题记
近日,连续接到好几个电话,都在询问记者曾采访过的一个老人的事情。这些电话又将记者带回到几年以前的一天下午。
那是2011年11月1日下午。
那天下午,我去看望一个老人。
而这个老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
所以,当我走进他曾经住过的那套房子时,并没有看到这个老人,但我仿佛看到了他的影子。
这是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应该有110平方米以上。有两间小房间里各支着三张床,都十分破旧,几乎所有的木床都曾反复修补,有几张木床的腿断了,就钉了两块小木板支着,那都是让农村牧区来的乡亲们留宿用的。还有一间小屋子是客厅,里面有一组三人沙发和几把破旧的椅子,沙发上方的墙上挂着两幅领袖的像,对面墙根里一个小柜子上放着一台老式的18英寸旧彩电——10年前,我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见过这台电视机。
剩下的一间屋子稍大点,那是他的卧室,他曾经睡过的那张木床,靠在一个临窗的墙角里,床头架也曾反复修补。挨着床的墙面上有几个地方的墙皮已经脱落,墙体裸露,用旧报纸糊了一下,还没完全遮住。床板是几块木板用钉子钉起来的那种,床板不平,就又垫了一些硬纸板。床边上立着一个带锁圈的破旧小柜子,柜子上有一部老式的电话机和一台现在很难看到的录音机,柜门上挂着一把铁锁。小柜子边上的墙角放着一个高一点的书架,它旁边靠墙放着一个劣质复合板衣柜,有一扇门快掉下来了……房间另一面的墙根里堆放着一摞报纸……这几乎就是全部了。整个屋子里面看不到一件像样的东西。
对了,我差点忘了那个狭小的门厅。一进门,门厅右侧靠玻璃隔墙的地方,临时安放了一个小柜子,上面是一个老人的遗像,遗像前摆放着几样简单的供品和酥油灯。遗像上的老人依然穿着那件好像已经穿了一辈子的中山装。
单看这情景,你一定会想,在今天的城市里,这绝对是个非常贫困的家庭。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不是一个普通百姓的家,而是一个早在1950年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54年就当了县委副书记的领导干部住过的地方,你会怎么想呢?
如果我还告诉你,这个人还是个高级领导干部,早在1971年就当了省委常委,历任青海省常务副省长、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在省级领导岗位上在任22年之久,你又会怎么想呢?
如果我再告诉你,这个老人还不是这套房子的主人,这是他最后的日子里不得已临时借住的地方,你又会怎么想呢?
是的,这个老人就是尕布龙。一个牧人和公仆,一个从金银滩草原一路走来的放羊娃,一个从放羊娃一步步成长起来的高级领导干部。
13年前,我曾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采访过这个叫尕布龙的老人。
也不知为什么,自打听到尕布龙离世的消息,我一直细心地留意任何有关他的公众信息,包括讣告上的电话号码和生平文字表述中每一个精心推敲过的措辞。我一再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他一生孜孜以求的就是最终的一句评价?如果换一个人,我们会说,这是善终。而对尕布龙来说,是,也不是。是,这是他应得的,而不是,是因为他一生辛劳看重的是辛劳本身的意义,绝不是因为人们怎样评说一个人的辛劳,尤其是他这样一个人。
在我的心里,尕布龙更多的是一个善良的牧人,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和时间,他才是一个领导干部。只是,有很多时候,他把一个牧人特有的一种品质带到了那些特殊的场合和时间,所以才显得不合时宜。还有些时候,他一直以自己的努力试图实现一个领导干部成为一个普通牧人的可能理想。这是一个朴素的愿望,也是一次历经长久跋涉的特殊实践。既然他能从一个普通牧人变成一个领导干部,理所当然,也能从一个领导干部还原为一个普通牧人。就像一个农民的儿子到城里工作,退休之后又回到乡下务农一样。他从没想过,这种身份角色的转换会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因为,即使在位高权重的时候,他也始终没有忘怀自己就是一个牧人。
如果让我写一句话,作这个老人的墓志铭,我会这样写:“一个牧人一样的公仆,一个公仆一样的牧人。”
今天,当尕布龙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又有人约我写尕布龙时,我已经没有更多新的故事可以写了。而且,我不敢肯定,如果尕布龙泉下有知,他会不会还让我写这样一个故事。因为对他而言,所有的故事都已经结束。而对于我们、对于生者,重要的并不是怎样用不同的角度去讲述同一个故事,而是用怎样的一种心态去聆听和认知。
那么,我们会怎样聆听和认知呢?
2011年10月11日《青海日报》刊发的《尕布龙同志生平》中有这样的文字:“退休干部尕布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2011年10月8日凌晨4时50分在西宁逝世,享年86岁……”报纸上对他的经历进行了详细的罗列,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