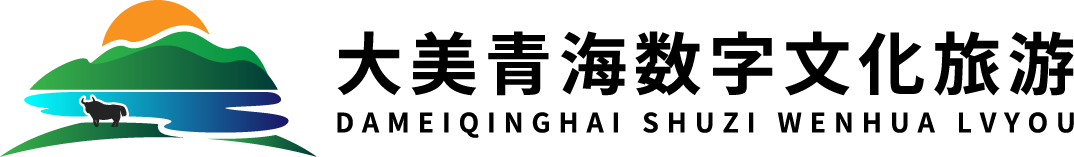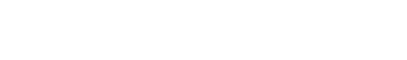三圣哲是吐蕃王朝崩溃逃到青海的藏饶赛、肴格迥、玛尔释迦牟尼三名吐蕃僧人,他们在湟水流域广传佛法,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宏传准备了条件,所以被后世尊称为“智者三尊”或“三圣哲”。
吐蕃松赞干布赞普时期,佛教开始传入雪域高原,并在吐蕃社会逐步传播。赤松德赞赞普时期建立了西藏佛教史上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正规寺院—桑耶寺。这座寺院由印度高僧莲花生大师和寂护大师仿照印度飞行寺的式样主持修建。桑耶寺建成后,最初有7人出家受戒,被称为“七觉士”。此后又有臣民子弟300余人出家受戒,并由西藏地方政府在寺内建立了一所妙法学校,有教师13 人,学生25人,僧人的一切费用由吐蕃王室供给。寺院中学习氛围自由,兼容并包,印度僧传授戒法,汉禅专修禅定,藏僧们学习声明(声韵学和语文学)。桑耶寺成为教育僧人的机构,应该说,它也是吐蕃历史上第一所宗教性质的大学校,开启了寺院培养人才的风气。
随着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寺院教育逐步开展起来。赤松德赞以后几位赞普继续弘扬佛法,佛教在藏区深入人心。到赤热巴金赞普时期,佛教在当时吐蕃社会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这位赞普崇信佛法,虔诚备至,他多次颁布法令推行佛教。为了大量而准确地翻译佛教经典,赤热巴金强制性对藏文进行了三次规范化的改革,并规定了“七户养僧”的制度,把僧侣抬到很高的地位,“所有大小朝政,皆请决于高僧;所有行政制度,也都以经律为准则。” 赤热巴金在厘定藏文,提高僧人地位的同时,又开办了律仪学院(慧、净、贤的传习部门),讲学学院(讲、辩、著的学术部门)和修行学院(闻、思、修的修行部门),并建立了30法部僧人的学习组织。这种有组织,有规章的寺院教育的出现,标志着吐蕃时期寺院教育体系的确立。
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要在吐蕃这一本教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安家落户,势必要遭到本教徒的激烈反对。吐蕃王朝后期几代赞普积极推行佛教的政策激化了佛教与本教的矛盾。赤热巴金赞普死后,崇尚本教的大臣拥立郎达玛继赞普位后,便开始在吐蕃地区实行恢复本教,打击佛教的政策。许多著名的佛教寺院遭到了关闭,大量的佛教经典被焚毁,大批佛教僧侣被迫还俗或被驱赶狩猎。郎达玛灭佛使藏区佛教惨遭厄运,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佛教在西藏销声匿迹100余年。佛教在与本教的斗争中虽暂告失败,但毕竟在这片雪域中撒下了复兴的种子。公元842年,吐蕃王朝末代赞普朗达玛(达磨)遇弑身亡,王朝内部势力分别拥立王子永丹和俄松,为继嗣赞普之位而相互攻伐。强盛一时的吐蕃王朝轰然解体,政权分崩离析,属部相继叛离。
郎达玛禁佛之时,在今雅鲁藏布江南岸曲沃日山的藏饶赛、肴格迥、玛尔释迦牟尼尚不知道佛教已经面临生死存亡。他们看到一些僧人被迫进山打猎,询问之后大吃一惊,立刻用骡子驮着重要的佛经逃离西藏。他们昼伏夜行,历经坎坷,辗转来到了当时称之为玛域的青海黄河谷地。他们先“居住于今尖扎县城北约40公里处坎布拉林区的阿琼南宗,一度活动于今该县加让乡的洛多杰扎岩等地,后移居今化隆县金源乡境内的丹斗地方,又一度活动于今乐都县中坝乡的央宗坪和今平安、互助等县的湟水谷地。”藏饶赛、肴格迥、玛尔释迦牟尼在这些地方潜心修行,传播佛法,由于郎达玛禁佛险遭灭顶之灾的西藏佛教在河湟地区开始复兴。著名高僧喇钦·贡巴饶赛就是在这一时期拜“三圣哲”为师的,并因其重要贡献而被誉为藏传佛教“后弘鼻祖”。
至10世纪末,随着西藏社会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各封建集团势力日益强大,新的统治秩序逐渐确立。佛教也作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和得力工具获得了复兴的机会,地方权贵开始迎僧建寺。“970年,西藏山南地区新兴的封建领主、达玛之子永丹的六世孙意希坚赞虔信佛教,听说青海丹斗地区有佛法流传,便资助鲁梅楚臣喜饶、热希楚臣迥乃、仲·耶希云丹等来自前藏和后藏的10人(一说7人)到丹斗,从喇钦·贡巴饶赛剃度出家。这些人经过数年勤奋修学,受比丘戒后,约于978年前后陆续返回西藏,在各地新兴封建领主的资助下修建了一批寺院,收徒传教逐渐形成寺院僧团,使藏语系佛教再度恢复发展。”西藏佛教也进入了的后弘期,并迅速成为了藏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佛教在西藏复兴之后,由于当时西藏社会内部相互隔绝,经济上缺乏内在联系,政治上又分裂割据,加上教法教理传承上的差异,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藏传佛教后弘期初,各佛教流派与称雄一方的封建实力集团结合,形成了藏传佛教各大宗派。从此,宗派利益与世俗利益混杂不分,它们在争夺‘正统’旗号下的封建割据斗争日益激烈。各宗派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纷纷向外发展,寻求新的‘化宇’,于是,藏传佛教文化冲破了内层区域的界限,植根于青藏高原边缘的许多民族中”。
藏饶赛、肴格迥、玛尔释迦牟尼长期在阿琼南宗、丹斗寺、平安白马寺等地修行并传播佛法,也使得这些地方成为藏传佛教的后弘圣地,在藏传佛教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据记载,他们三人晚年在西宁示寂,后人为保存他们的灵骨专门建造了灵塔,并以此为根基建造了西宁大佛寺。